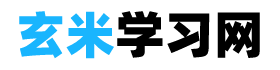灰娃,原名理召,祖籍陜西臨潼,1927年出生于“八百里秦川中部,一個綠蔭掩映、泉水琤琮的村莊,未及記事年齡隨雙親到了古都長安。父親在中學教書,母親在家操持家務”。1931年入陜西省西安師范附屬小學讀書,一直讀到六年級。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為躲避戰火,灰娃隨家人遷往距西安百來里之外的一個村子暫居。1939年,被姐姐和表姐送往延安,進入“延安兒童藝術學園”學習音樂和戲劇,從此開啟一段嶄新的人生旅程。當時的延安不僅是戰爭的后方,還是文化藝術的“大后方”,這里聚集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者、作家和藝術家,比如艾青、何其芳、嚴文井、冼星海、杜矢甲、張仃、蔡若虹等,灰娃在這里受到了良好的文化藝術熏陶。1946年,灰娃與八路軍新四旅作戰參謀武昭峰結婚,隨部隊轉戰晉冀魯豫地區。1948年,患肺結核前往南京治療,1951年轉至北京西山療養院,同年,丈夫武昭峰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1955年,灰娃身體初愈,考入北京大學,曾在俄羅斯語言文學系學習。1960年被分配到北京編譯社做編輯,后又因病提前退休至今。1964年,與開國少將、戰爭史專家白天結婚,這段婚姻持續到1974年白天因病逝世。1966年“文革”開始后,灰娃陷入了精神分裂,持續六年之久。

灰娃
1972年,在醫生看來,灰娃已經恢復健康。但外人無法真實“勘探”出她內心深處的恐懼、疑惑、憤恨、絕望和悲涼,于是,尋找心靈出口的她嘗試通過寫詩排遣悲情。最初她為自己寫的“東西”感到恐慌,私下猜想著肯定有人會用什么新式武器探測到她寫詩的秘密,她常常把剛寫完的詩作撕掉、扔進馬桶沖掉。這種邊寫邊撕的狀態直到被張仃發現才停止。張仃是灰娃在延安兒童藝術學園求學時的美術導師,新中國成立后因同住北京,經常來往,他及時、敏銳地捕捉到灰娃的詩才和靈性,并建議她將內心美好的感受寫出來,把詩當作美的出口。受到鼓勵的灰娃從此將寫出的詩裝在鐵盒子里,埋在花盆下,直到1977年春,她才敢把詩稿取出來示人。這段時間保留下來的詩作有《大地的母親》《無題》《心病》《路》《水井》《我撒手塵寰……》《土地下面長眠著——》《墓銘》《我額頭青枝綠葉……》《不要玫瑰》《只有一只鳥兒還在唱》《我怎么能說清》《帶電的孩子》《童聲》《己巳年九月十二日》《鴿子、琴已然憔悴》《穿過廢墟 穿過深淵》等。
灰娃曾言:“我所有的文字,都是我的生命熱度、我情我感體驗的表達。”灰娃開始寫詩時已經45歲,在此之前幾乎沒有任何寫作經驗,但人到中年的她借由詩歌得以釋放內心的焦慮,從精神危機中逃脫出來,獲得了靈魂的自我拯救。自此,灰娃矢志不渝地在詩歌寫作生涯中砥礪前進,持續創作的熱情至今未盡,每一首詩的創作都帶給她“心靈洗禮的感召震撼”,恰如她創作于2020年的《帶著創傷心靈的芬芳》一詩所寫:“難得的日子,仿佛一只相思鳥兒/躲進荼靡花叢幽寂陰影/與自己聊天、憶往,夜夜走入無從察覺/銷蝕關于人、關于靈魂記憶的噩夢/被經受污名、人性摧殘穿越時間/感恩宇宙大神賦予我向神靠攏天性/獨自和天使的憂郁哀詠低涌于廢墟/暮靄里神的信使夜鶯、秋水仙的歌/神秘、空靈、忽隱忽現振蕩于蒼穹深處/你聽見心靈洗禮的感召震撼嗎”。在與命運的沉浮相逢時,她“逆風前行,攜帶覺醒激情”(《那瑣細無名的思念》),并及時記錄下每一個“短暫的詩意體驗”(《帶著創傷心靈的芬芳》)。她警示別人和自己,“夢碎之人,莫把年華耗盡”,“聽那自由歌后百靈之春時隱時現/隔溪余韻悠揚飄忽/星星之火也在擴展光焰”(《懷鄉病》),或者選擇“神一樣,從冰藍的光氣穿越/沉浸在迷迭香靈芬的神秘清馨/聽自己良心以沉默言說”(《愿命運依然見證》)。“我最初的夢,我依然愛/我的星辰,照臨我第一束光/喚醒我的牽掛,我的眷戀/我的愛與痛,我的怕與驚……”(《綠天堂》)灰娃的人生經歷具有濃郁的傳奇色彩,如果說她的前半生是站在“信風中/喂養沉默無花的果實”,她的后半生則是“織一襲騎馬來的春光/整個大地全通向彼此”(《山山》)。她的詩歌不僅“可以看作是她‘一個人的心靈史’”,還在當代詩壇上具有特殊意義,研究和考察她的詩歌創作歷程,無疑具有文學史的意義。
灰娃的個人經歷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階段:延安時期的童年生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至“文革”期間精神分裂時期;新時期與張仃結為伴侶;張仃逝世至今。灰娃自“文革”后期開始寫詩,她每個人生階段的詩歌創作都如其創作于2019年的《懷鄉病》一詩中所言,“生命密碼已編織成斑斕悠長的日子/銘刻在心上,譜寫在歌里”。
時代的病癥:“我鬢角額前星星綴滿”
灰娃于1966年患上精神分裂癥,70年代在患病的情況下非自覺地開啟了寫作生涯,在此之前灰娃幾乎沒有寫作經驗。最初,詩歌創作對她來說是釋放內心焦慮的一個出口,是治療病痛不可或缺的“良藥”。因為詩歌,她得以在非現實的世界中找到靈魂的寄托,最后竟神奇地從精神分裂的危機中康復,她的詩歌帶給讀者心靈的洗禮和美的享受。榮格把“藝術創作方式區分為心理學的和幻覺式的”,“心理學式的創作從人類意識領域中尋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現實的藝術家,幻覺型藝術則從潛藏在無意識深處的原始意象中尋找素材,因而是背對現實、面向自我的藝術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灰娃的詩歌創作屬于幻覺型藝術,她本人則是典型的“背對現實、面向自我”的詩人,她是鮮有的在不自覺中完成個人主體性回歸的創作特例。
灰娃在少年時期經歷了殘酷戰火的洗禮,也接受過紅色革命教育,從成長經歷看,她應該能很快適應新的環境,投入新的學習和工作。但真正走上工作崗位之后,她反而發現自己的思想和行為與當時的大環境格格不入。進城后,灰娃發現她周圍的環境和人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實的力量對于從兒時起就喜歡對著星星、銀河歌唱,喜歡睡在自己種植的花草旁邊的灰娃來說是一種精神的踐踏,她無法從根本上接受虛假的“真實”。
社會現實的狀況令灰娃費解,她的單純、敏感、特異同樣令一些人無法理解和接受。日復一日,緊張的神經終于繃不住,灰娃陷入精神分裂。“文革”開始之后,她愈發不堪承受壓抑,為了排解苦悶,她不由自主地把郁積于心的感想寫下來。從榮格對精神病人的分析可以找到灰娃發病的根由:“精神病理學告訴我們,有一種精神紊亂就是起自病人把自己與現實割裂開來,越來越深地陷入他個人的幻想之中,結果,現實力量的失勢導致了內心世界決斷力的增長。”思考空間被規約、觀點被束縛,而詩人靈魂里卻充溢著澎湃的情感,不斷涌現出來的矛盾不時沖撞她敏感的心扉。最終這些情感借助詩歌表達出來,淤積在詩人心中的愁思亂緒得到了疏通和釋放,焦灼憂慮的心靈在詩的世界里獲得暫時的安寧。
灰娃自小就“朝思暮想著兩件事:旅行、作曲。將心靈對大千世界的奇妙感悟訴諸管弦。幻想中自己應是貧苦的,買不起蠟燭,月光下坐在屋頂上編織音樂”。如此浪漫的理想只屬于純真美好的心靈,她始終葆以質樸之心捍衛世間的“真”和“美”:
我鬢角額前星星綴滿
我為厚道的心呼號用嘶啞的嗓音
即使世間沒有感應沒有回響
也壓根兒就沒有真這件事情
——《墓銘》
詩人在現世中無法訴說無限的傷心委屈,只好轉身,背對懸崖迎著黑暗獨自上路:“生而不幸我領教過毒箭的分量/背對懸崖我獨自苦戰”(《墓銘》)。無論是被毒箭重傷,抑或被曾經的信仰欺騙和遺棄,詩人都陷入了孤獨的絕地。在現實生活中,生命受到禁錮,精神得不到自由,追求美而不能,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反差促使灰娃拿起筆,詩歌成為精神的避難所,使受難的靈魂得到慰藉。
“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雖說“文革”中很多詩人都有著坎坷的人生際遇,但像灰娃這樣為尋找靈魂出口而不自覺拿起詩筆走上自我救贖之路的創作行徑尤顯特異,這些文本為當代詩歌史提供了別樣的視域,也打開了女性詩歌寫作的新面向。
詩神的眷顧:“我們蹣跚人間緊擁磨難”
灰娃開始詩歌寫作之前,幾乎沒有任何寫作經驗。當愁緒和郁悶無法排遣時,她才開始隨意涂寫,從一個字、一個詞到一個短句、一段話、一首詩……逐漸地積累下來,直至后來結集出版,這也是灰娃被視作“自我教育”下的“素人詩人”的原因。榮格曾闡釋藝術和藝術家的關系:“藝術是一種天賦的動力,它抓住一個人,使他成為它的工具。藝術家不是擁有自由意志、尋求實現其個人目的的人,而是一個允許藝術通過自己實現藝術目的的人。”灰娃就是一個被詩歌之神“抓住”的人,她自覺而清晰地詮釋過自己的創作心理和寫作過程:“某個時候,心里有種旋律、節奏顯現,不知不覺日益頻繁在心里盤桓,無論走到哪里,無論做什么事,這音樂總揮之不去,音樂執意占據心靈,控制心靈。隱約中有異樣感覺,這時,受此音樂催促,以文字釋出,呈示為人們稱之為詩的這種形式。然后刪改,盡力改好些。”灰娃的詩不落俗套,浸透著神秘韻味,詩才天賦處處流露。
縱覽中外女詩人的創作歷程,詩總是與青春結緣,茨維塔耶娃18歲時就自費出版了詩集《黃昏紀念冊》,阿赫瑪托娃23歲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黃昏》,冰心讀大學期間就結集出版了小詩集《繁星》和《春水》……古今多少才華橫溢的詩人年少時即自覺以詩練筆,寫作風格在創作中也逐漸成熟。灰娃則不同,她中年開始寫詩,自始即形成了比較成熟穩定的風格,即她寫詩先形成詩的旋律或節奏,然后跟隨著它們再將詩情或詩思落于筆端。誠然,與當代很多女詩人相比,灰娃不是多產的詩人,因為她的每一首詩都來自靈魂深處,唯心靈受到牽動方能起筆,并帶領我們走入一片無人到訪過的奇異境地。
天生的敏感細膩注定了灰娃的孤獨和寂寞,這導致她一度成為常人眼中的“另類”。她曾在詩中暗示過她與現世的無法溝通:“我們的手臂□人說是鐘情熱切/我們蹣跚人間緊擁磨難/過路者都把這浩大悲壯/把這隱痛□輕笑閑談”(《路》)。
詩人見識了生活中疊加的虛假與謊言,滿腹的委屈和“隱退”之心無法向俗世里的人們傾訴,一顆本真質樸的心籠罩在濃重的孤苦煩悶之中,因而有詩句“我們蹣跚人間緊擁磨難”。但正是這“孤獨與寂寞,對外有助于默觀默查,有助于更深沉更冷靜地觀照社會;對內有助于自省反思,徹悟人生,凝聚內心的生命力”,使得詩人對自己曾經堅守的信仰、對現實和人性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繆斯選擇了灰娃,把灰娃引入詩的苗圃,猶如種子遇到陽光和土壤,又如同泉水找到流瀉的出口,詩人終于為自己內心積蓄的焦慮和形形色色的美找到了傾吐的渠道,她憑借精神直覺直抵作品深處,挖掘分裂的自我和駁雜的情感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她對內心幻象的正視和處理也是她對自我生命的反省。
結語
灰娃的特立獨行不可復制,她的詩風在當代詩壇極具標識度。其詩歌風格既奇麗又矜持,審美既古典又現代,詩品既清明又神秘,思想既單純又豐厚,感受既奇詭靈動又充滿人間煙火氣,藝術表現手法既浪漫又超驗,語言既凝重苦澀又清峭唯美,想象既無拘無束又充滿野性。她因患病寫詩,因詩而從精神病態走出,生命力愈發強勁,她的詩歌寫作可以看作是對權力話語控制的反抗以及自我治療。她在這種“治療”中創造出一種全然個性化的詩歌話語系統。尤為可貴的是,九十歲高齡時,她仍堅持寫詩,在詩歌題材、意象、風格和表現力等方面均有新變。從小到大,灰娃“心里就裝著一個字——美”,創作四十余年,她篤定地秉持著自己的詩歌觀,創造出神秘瑰奇的生命境界。灰娃的詩率真,具有攝人心魄和精神自救的力量,她為女性詩歌提供了新的精神資源。